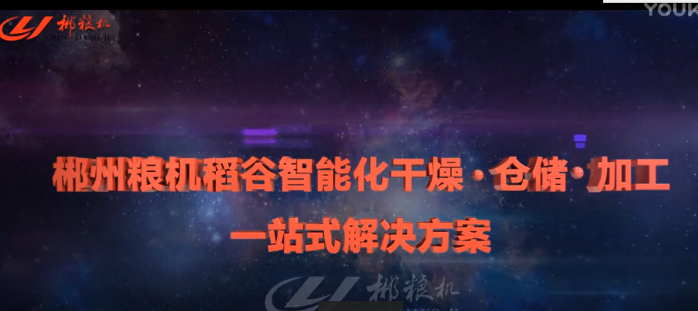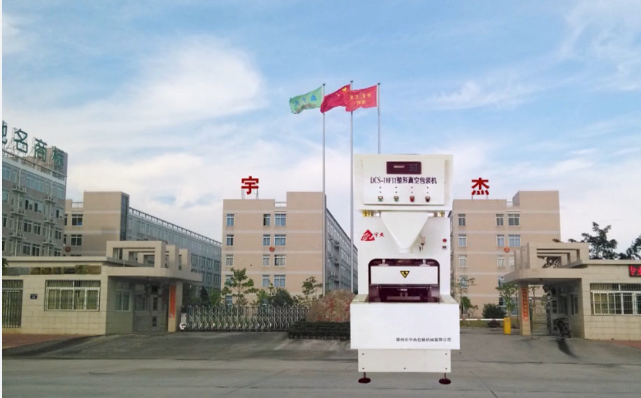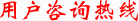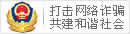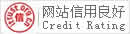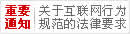實際上,自2002年《轉基因食品衛生管理辦法》、《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文件出臺至今,轉基因產品標識制度施行已有12年,卻面臨執行難的多重問題。問題背后,則是政治、科學、經濟的多重博弈。
規定 零容忍 中國版本“最嚴厲”
“我們要求明確標注,并不是要反對轉基因,也不是針對某一家企業的產品。”8月15日,云南同潤律師事務所律師許思龍在微博上公布了反對“轉基因食品標識不顯著”行動,旋即獲得數十名律師的聯名支持。
“我們的訴求就是標識應該明顯、醒目,但實際情況是,很多超市里的轉基因食用油標識非常不明顯。而且我們調查發現,現在標注轉基因的食用油比前兩年還少了,這讓我們擔憂,到底是轉基因的油少了,還是它們不標了?”許思龍指出,《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和《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等多項法律法規中,都規定轉基因食品應該在產品標簽的明顯位置上標注。
對于許思龍等律師的維權行動,民間不乏贊譽之聲,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的今日,“轉基因”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技術語匯,無疑加重了公眾的疑慮。再加上層出不窮的“轉基因危害健康”謠言,讓公眾“談轉基因而色變”。
在此背景下,要求“知情權”成為消費者順理成章的訴求,“知情權”甚至升格為某種擁有政治意味的詞語。許思龍表示:“轉基因的安全性雖然存在很大的爭議,但是我們不涉入這個話題,我們主要是針對這個消費者知情權這個問題,消費者買不買,是他自己選擇的問題。”
要求轉基因產品標識,也并非中國特有的規則,諸多歐洲國家及澳大利亞等國,都有相應的標注規則,如俄羅斯相關規定,含量超過0.9%轉基因原料的食品必須加帶標識;而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出售的轉基因食品,無論是整件食物,還是只用于食品加工的材料之一,如果添加的基因材料或蛋白質會存在于最后的食物中,必須獲得轉基因情況證明。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對于轉基因標識的管理制度是世界上“最嚴厲”的,因為國外要求轉基因產品標注的同時,往往會規定轉基因原料在產品中的比例閾值(yù zhí,指的是觸發某種行為或者反應產生所需要的最低值),超過閾值才需標注。而我國的相關規定并未對轉基因原料在產品中的比例進行規定,也就是“包含既標注”,這一強制標識制度被稱為“零容忍”或“0閾值”。
標準 不統一 至今無科學依據
看似嚴格的“零容忍”政策,卻是政策漏洞的發端,無論是研究轉基因技術的科學界,還是涉及轉基因產品生產的企業,都曾對“零容忍”政策發出過質疑。中國水稻研究所生物工程系教授王大元的觀點頗具代表性–“零容忍”標識法在事實上不可執行。
“中國的轉基因標識法采取了零容忍政策,看起來是全世界最嚴厲的了,但實際上這有點糊弄那些反轉人士。”2014年7月,王大元撰文《轉基因標識法的尷尬》,指出轉基因標識存在多種問題。
王大元指出,目前諸多食品均含有轉基因成分,如軟性飲料多含有轉基因玉米成分,但這些產品從未標注“轉基因產品”;而無糖食品中常使用的甜味劑阿斯巴甜,也是由轉基因大腸桿菌發酵而得,亦從未有人要求對阿斯巴甜做標識。
即便增加對轉基因成分閾值的規定,轉基因標識也存在無科學依據的問題,“歐盟的0.9%、日本的5%、韓國的3%以及中國的零容忍。這些標識的根據是什么?為何你要0.9%,他要5%,沒有一個科學家說得清楚。”
尤其在轉基因產品日漸滲透到公眾日常生活中后,轉基因產品標識其效力越來越低:“反轉者可以選擇不買標識有轉基因的大豆油, 但飯店或單位的食堂都是用轉基因大豆油炒的菜,豬和雞也是吃轉基因大豆飼料喂肥的,難道你到飯店去吃飯時,服務員端盤子上菜時還要嚷一聲,‘轉基因魚香肉絲一盤’?”
在許思龍看來,科學技術上的爭議,不能掩蓋消費者“知情”和“選擇”的權力,而采取“零容忍”的規定,正好可以解決標準不統一的尷尬:“只要有檢測技術,檢的出來的就要標。而且除了檢測標準,還要從商品的原材料追溯入手,從各種材料的進貨渠道進行監管,有轉基因的原材料,成品就應該標注。”
原則 易誤導 涉嫌不合理歧視
在支持轉基因技術的人群中,還有一個更為“激進”的觀點,同樣擁有廣泛的支持者–不是如何標注的問題,而是壓根不應強制標識。
反對轉基因產品強制標識者的一大有利論據便是,一向走在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前沿的美國,至今不要求強制轉基因標識,采取自愿標識政策。這一事實在著名媒體人崔永元的表述中,是“美國人稀里糊涂地吃了17年轉基因”。
轉基因標識容易產生誤導,是美國拒絕轉基因強制標識的一個主要原因。據媒體報道,國際食品信息委員會國際關系副主任安迪?本森曾解釋美國FDA(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對于食品標簽的原則:“標簽不應該造成對已經證明是安全的食品的不正確的負面理解,標簽上的所有表述都應該公平、開放并且得到大眾的正確解讀。”
FDA表示,沒有發現證據顯示轉基因食品“不同于其他傳統食物,或者新技術開發的食品比傳統育種植物有更大的安全問題”。既然通過轉基因生產的食物和傳統食物沒有實質性的區別,那么就沒有給轉基因食品貼標簽的必要,該原則被稱為“實質等同”。
這也是公眾認識與科學觀點最大的鴻溝所在–在公眾眼中,轉基因的安全性仍然未知,乃至在主流媒體中,也常常見到“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爭議”的字眼。
至于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等權威科學機構稱轉基因作物“是有史以來進入我們食物供應的最為徹底測試的作物”,只會被看作科學怪咖哄騙公眾的又一大例證。
而在鴻溝填平之前,消費者很難想象,轉基因標識與轉基因安全沒有任何關聯,一種更容易被消費者接受的觀念是:轉基因產品之所以被標注,是因為它們的質量比非轉產品差。
轉基因技術的支持者擔心,這種消費者觀念上的誤區,導致轉基因產品受到市場歧視,甚至被迫從市場退出,其最終的受害者,仍會是消費者本身。
“轉基因標注最大的問題是變相歧視。試想,如果有人討厭河南人,要求所有食品都強行標注制作人是不是河南人,你會同意嗎?”科普作家袁越以寓言故事的形式,描述了轉基因標識制度的不可行,其核心仍然是標識制度給消費者帶來的負面引導,“目前已經被批準上市的轉基因食品沒有任何安全問題,強行標注的話會讓老百姓認為這種成分不安全,拒絕購買,從而給開發商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久而久之,轉基因的研發動力就沒有了,這就是歐洲面臨的情況。”
有趣的是,支持轉基因標識的消費者,并不會要求產品中標注原材料噴灑了農藥或使用了化肥。
成本 增成本 消費者為選擇付費
在諸多反對或支持轉基因標識的觀點中,一個因素往往會被忽略–轉基因產品的標識勢必帶來產品成本的提高。
2014年4月,美國農業科學與技術理事會發布名為《美國基因工程食品強制標識的潛在影響》的調查報告,從法律、經濟等多個角度調查了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帶來的影響,報告中指出,雖然信息豐富有助于消費者根據慣有喜好進行選擇,有機食品和非基因工程食品為有成見的消費者提供了信息和選擇,但它們往往比傳統食品更昂貴;強制標識也會帶來多方面的成本。
有機食品的高成本,來自于其低產、有隔離成本以及在買賣過程中證明其可靠性的各種測試、認證和追溯成本。例如,近年美國非基因工程玉米和大豆的生產商所接受的價格,要比傳統商品生產商平均高出15%。
強制標識也會帶來成本的提高,除了原材料的追溯成本外,標識帶來的市場影響,也是企業最為擔憂的。美國農業科學與技術理事會指出,食品生產商可能為了迎合消費者的需求,替換原料以降低轉基因成分,但使用非轉基因原材料的成本,最終還將由消費者承擔。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未必是那些喜愛有機食品,愿意付出高價的中高收入者,而是那些原本有更低廉商品可以選擇的低收入人群。
盡管存在著諸多爭議,并非所有“挺轉派”都反對轉基因標識,英國著名科普作家馬克?林納斯便認為,推廣轉基因標識,很有可能成為公眾認同轉基因的“鑰匙”。
“正因為這個行業全線防守以避免告訴人們哪些食品含有轉基因成分,所以人們越來越害怕轉基因,這有可能是史上最糟糕的公關策略。”馬克?林納斯建議,轉基因標識應以國家層面強制運行,涉及所有行業,需要排除對健康和安全問題的暗示,而且應該包括糖、油等一系列衍生品,這就意味著“貨架上80%的食品都要標識”:“神秘萌生恐懼,熟悉帶來接受與理解。一旦消費者熟悉大多數食物里都含有轉基因成分的事實,他們會意識到,這項技術是安全的,它可以提供一些他們真正想要的東西。”


 公告信息:
公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