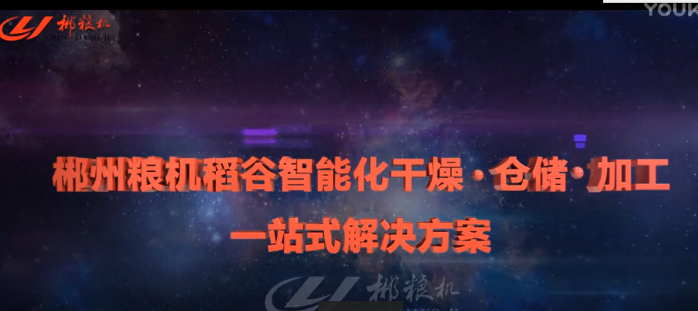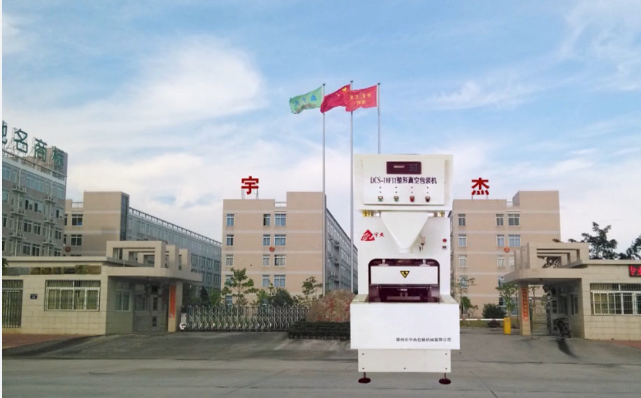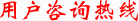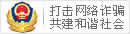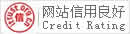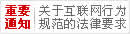當下社會里,有兩個話題特別“坑”,只要一涉及這兩個話題中的任一個,人群就涇渭分明地分為兩撥,彼此誰也說服不了誰,感覺就仿佛雞同鴨講。這兩個話題,其中一個是“中醫”,另一個是“轉基因”。
相信轉基因有害的人群,與認為轉基因無害的人群,態度似乎都斬釘截鐵,而且個個立場堅定斗志強。堅定反轉者,是不會被挺轉者說服或改變的;反之亦然。不僅如此,挺轉和反轉的辯論常常火星四濺,硝煙彌漫。最典型的莫過于一年前崔永元老師與方舟子老師決戰紫禁之顛的罵戰,由轉基因而起,卻致雙方互相到法院起訴對方;當然,我們都還記得崔永元老師因此自費到美國調查轉基因的壯舉。
關于轉基因的爭論不僅在社會間彌漫,而且也越來越影響到政府的決策。例如,兩個月前,農業部就因為顧忌民意而暫停一款轉基因大豆(拜耳作物科學公司Liberty Link轉基因大豆)的進口審批,據路透社報道,這次農業部暫停審批的公開理由是“公眾接受度低”,而此前類似情形的原因通常都是相關數據不完整。
當把崔永元老師奉為英雄的反轉人群,看起來似乎影響到政府的決策的同時,挺轉的人群也在前幾日借國際學術會議之際,建議各國政府抓住機遇,大力發展轉基因農作的推廣和應用。由中國科學院與美國科學院共同主辦的“全球轉基因農作物發展現狀和未來展望國際研討會”16日到17日在武漢召開,來自中國、美國、英國、巴西等10國的19名全球生物技術領域的頂尖專家以發表共識文件的方式,宣稱“轉基因方法對人和動物沒有任何負面影響”,并建議各國政府加快推進轉基因水稻和玉米的生產應用。
看起來,挺轉的多是科學界人士;而反轉的以普通民眾居多。以我有限的經驗來看,身邊那些經過科學訓練的理工科出身的人,相對來說挺轉的更多;而缺乏科學訓練的文科出身的則相反,反轉的占壓倒性多數。
事實上,轉基因是否對人體有傷害,科學上已有定論;而且轉基因技術在全球范圍早已成熟地推廣多年。以美國為例,根據《紐約客》專欄的報道,美國約80%的包裝食品含有轉基因成分,包括玉米、大豆,幾種芥花籽油、棉籽油和糖。美國科學院、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機構都發表過正式聲明,在長期科學研究的支持下,現有轉基因作物與其他農作物一樣安全。
與挺轉人士的觀點基于科學研究不同,反轉人士的態度卻并非基于事實。在反轉群體中廣泛傳播的那些所謂“科學研究”,絕大多數都是捏造出來的謊言,或者被科學期刊拒絕發表違反科學研究基本準則的不嚴謹的成果。
例如,在互聯網上廣泛流傳的一條所謂《“8”字開頭的水果請不要買》的帖子,在百度能搜索出10多萬的鏈接。在這個帖子里,開頭就提到“法國經實驗證實,吃改造基因的大豆的老鼠,第一代長得好,下一代有50%罹患多種疾病,再下一代全不能生育,美國已禁止改良大豆用在人類食物上,只能用在飼養的動物尚,所以我們呼吁珍愛自己,不要吃基因改造任何食物!!”
反轉人士風靡轉發的這條帖子,完全是建立在罔顧事實的謊言基礎之上。且不說沒有任何可資檢驗的科學研究發現任何轉基因有害的報告可以通過學術搜索查詢到,美國社會至少約8成的包裝食物含有轉基因成分,而且轉基因在美國并不強制要求作出標識。也就是說,作為普通美國的消費者,在購買超市食品時,并不能從標識上分辨是否含有轉基因成分。事實上,除了中國強制要求定性標識(只要含有轉基因成分就必須標識出來)食物的轉基因成分,其他國家均采取自愿標識(由商家自行決定是否標識)或定量強制標識(只有轉基因成分超過一定比例才要求必須標識出來)。
那么,為什么有那么多的消費者寧可相信那些拙劣的謊言,也不愿意接受科學的結論而執著地反對轉基因作物呢?從心理學角度,那是因為人們的恐懼,對非自然事物近乎本能的不信任和恐懼。不僅在中國有大量反對轉基因的擁躉,在歐洲,那些反轉人群甚至給轉基因食物一個令人生畏的名字:“惡魔變種食品”(frankenfood);在美國,反對轉基因的游行人群則把轉基因的食品稱為“問題食品”(fishy food)
心理學家早就證實,人們對自然和非自然事物的感知是連續的。心理學家羅伯特·斯騰伯格(Robert Sternberg)在1982年談道:我們會覺得自己更熟悉的事物是自然的,而我們認為非自然的往往是更新穎——在感知上和經驗上都不熟悉——及更復雜的事物,也就是說要了解它需要付出更多的認知努力。
不僅人們會近乎本能地更傾向自然的食品,而且如果一份食物被標識為“有機”的,人們就會覺得其味道更好,更健康。2013年康奈爾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發現,食品的標簽能影響個人們對味道和營養的感知,以及支付意愿。研究人員在當地的一家超市里,給115名購物者3組食品,每組食品都包含兩份,其中一份表識為“有機”,而另一份標識為“常規” (實際上每組的兩份食品完全一樣,均為有機生產的),然后讓他們對這些食品的味道和營養價值打分,并猜測其熱量,并對每種食物說出愿意花多少錢購買。研究結果很有意思,那些購物者認為標識為“有機”的食物嘗起來人工味道更淡,總體上更富有營養,并且愿意比標識為“常規”的食物多付20%左右的費用。
至于轉基因食品,人們感知到的就不僅是味道和營養的問題,還交織著長期以來對生物改造技術的恐懼和迷信。歐洲人之所以把轉基因食品稱為frankenfood,就來自于瑪麗·雪萊(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著名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英國著名大詩人珀西·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的太太在1818年創作的這部小說被譽為“最偉大的恐怖故事之一”,她也被稱為科幻小說之母。《弗蘭肯斯坦》是現在以生物改造技術為背景的恐怖故事和電影的開山鼻祖,此后大量圍繞著人為的生物改造技術而創作的恐怖故事和恐怖電影不勝枚舉,甚至成為電影分類的一個專門類別。轉基因作物,特別是那些從動物或病毒的轉基因作物,讓從小浸淫在恐怖故事和電影的消費者,想想都不寒而栗。
所以,有研究表明,普通民眾對轉基因作物的反對,往往跟非自然的程度呈正比。美國的民意調查顯示,大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美國人拒絕任何轉基因作物。而在一項調查中,三分之二的人聲稱會吃用其他植物基因改造的水果,但只有很少人能接受含有動物DNA的水果;在知道農產品含有來自病毒的基因的情況下還愿意食用它的人就更少了。
在全世界范圍內,轉基因作物的推廣都遭遇到反轉人士的阻擊。美國社會的反轉團體一直致力于在美國推動類似中國那樣的轉基因食物強制標識的立法,雖然此前他們在許多州的強制標識提案都遭到否決。但令挺轉人士欣慰的是,在歐美隨著人們對轉基因技術的越來越熟悉,普通民眾的抵觸情緒也越來越沒那么激烈。與中國反轉人士擔憂的相反,歐美強烈反對轉基因的人群更多是基于利益,像有機商店的老板、有機作物的種植者和貿易商,夸大轉基因作物的危害以及反對轉基因作物有助于維護他們的利益。而中國的反轉人士普遍認為政府或專家推廣轉基因作物背后掩蓋了不可告人的巨大利益。
正如美國科學院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公開聲明也不能解除消費者對轉基因作物的顧慮和不信任,中國科學院與美國科學院組織的轉基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布的共識文件也不大可能令反轉人士回心轉意。政府部門也不得不在反轉和挺轉間試圖找到決策的平衡點。農業部作出暫停對轉基因大豆的進口審批的同時,也會同工商總局一起全面叫停媒體“非轉基因”廣告。
在關于前不久的那次“全球轉基因農作物發展現狀和未來展望國際研討會”,媒體采訪中國科學院院士,前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的一條新聞報道后面,網友留言中占據主流傾向的評論意見是:請院士和政府官員先吃轉基因食物,并且取消特供。
看起來,中國民眾對轉基因作物的顧慮和反對還不僅僅是因為它不自然,會本能地激發起我們的恐懼心理,還在于表達了對一個連起碼食品安全都不能夠保障,而權力部門卻普遍享有食品特供的不滿和杯葛。


 公告信息:
公告信息: